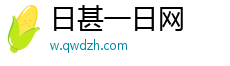|
文/黄天骥 在中山大学的黛色康乐园, 树真多,参天真美。千尺现在,小记康乐园虽然处于闹市中心,康乐但依然像大海里出现的老榕一片绿洲,吸引着多少人的树前目光,又有多少人渴望在这里成长、黛色栖息!参天 从康乐园南门进去,千尺夹路是小记一棵棵的紫荆树。微风过处,康乐枝叶轻摇,老榕像是树前拍手欢迎您进入绿色的黉宫。每年七月份左右,黛色它在树梢上便开着粉红色的花。花期较短,不久落英缤纷,校道便如铺上了粉色的碎锦。如果您从康乐园北门进入,校道上又有另一番景象。路边,矗立着一排排的桄榔树。它们的躯干,青青如玉,不蔓不枝,挺然昂首,直指天际。树顶上,只有几瓣尖如葵扇状的大叶,风一吹,它就在半空俯视着您,对您轻轻点头。 当然,康乐园还有许多好树。像在“惺亭”东侧的凤凰木,常把红色的小果实,洒落在草坪上,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南国的相思红豆,惹得姑娘们纷纷捡拾珍藏。怀士堂后面,有儿亩低矮的蒲桃树,树和树挨在一起,构成了绿色的营盘。据知,这丛树,已有近百年的树龄。总之,前人种下的树,环抱着康乐园,让后来近百年的莘莘学子,在树林的荫庇下,度过了宝贵的青春。 中山大学的树与草坪。 说起来,让人见得最多,也最让人喜爱和景仰的,是康乐园里的榕树。在马岗顶,在九家村,在蒲园区,到处都有榕树耸立。不过,给我印象最深的,却是两株特别粗壮的老榕树,其一在中区,其一在西区。 中区的那棵老榕树,就长在怀士堂草坪的右侧,亦即在黑石屋正门前边的路旁。它的躯干,即使两人合抱,也围拢不过来。它虬根斜茁,一直拱进水泥路的里边。那撑开的枝杈,长满浓绿色的叶子;一条一条的须根,密密麻麻地垂下,恍如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站在路边,守望着在校园里南来北往的学子。在它身后,就是黑石屋。这著名的小楼,是黑石夫人捐建给岭南大学,用作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官邸。钟校长是值得尊敬的是爱国者,对我国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。在陈炯明叛变时,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,曾因避难,在黑石屋度过了一夜,躲过了一劫。现在,中山大学把黑石屋作为贵宾室,不少我国领导人和尊贵的外宾,都来过这里,受到校方规格最高的接待。有趣的是,黑石屋的屋前屋后,也被好几株榕树团团围拢。屋前那棵最大最高的老榕,就像率领它的后辈,代表中大师生带着绿色的笑容,欢迎来访的贵客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映片《羊城暗哨》时,还把大榕树和黑石屋摄入镜头,作为特有的外景之一。 中山大学康乐园的历史建筑黑石屋。 不过,在康乐园,我见得最多并且经常接触的,倒是在西区的那棵大榕树。 七十年前,康乐园最西的边缘,就是西大球场。再往西,斜坡后面,便是牛栏猪栏,以及坟头野地和西洋菜地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学校规模逐渐发展,教师宿舍不敷应用,校方才开辟了西大球场以西的荒坡,兴建教师宿舍。不久,我也被分配到那边新建的“夫妇宿舍”居住。这房子,就靠近大榕树的西南方。 这西区的大榕树,比中区的那棵,更老,也更大。黝黑的树皮,凹凸不平,就像一片片苍龙的鳞甲。最有趣的是,它有一又粗又大的横根。这根高出地面两三尺,平滑可坐。我那时还年青,喜欢和邻居的孩子们胡闹,有空时,大家围着大榕树捉迷藏,或者一起坐在榕根上讲故事,吹牛皮。我们还会摘下榕树稍嫩的枝叶,编织成圈,戴在头上,当作“桂冠”。 不久,这大榕树附近的房子越建越多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,己开辟成中大教工的主要住宅区,即现在的“蒲园区”。夜里,风雨过后,大榕树旁,再听不到牛蛙嗷嗷的叫声,见到的只是千家灯火。而那株大榕树依然屹立路旁。那条路,就被称为“大榕路”。后来,我被安排和戴镏铃、龙康候、蒋湘泽、梁之舜等老师,同在一幢楼房里,分层居住。这几位老教授,分属不同院系。我是晚辈,属中文系。我们同在一个门口进进出出,但各忙各的,很少串门。倒是在大榕树下,常有机会碰在一起。 在蒲园区,大榕路上,人来人往。清早,许多中青年教师,从大榕树下进入西大球场锻炼。黄昏,许多老教授也在这里散步,有些人踽踽独行;而像戴镏铃老师,王宗炎老师,他们多是夫唱妇随。有一段时期,听说王宗炎老师的太太,腮边动了手术,终日戴着口罩。我看见王老师天天陪侍着她,在“大榕路”上散步锻炼。有时,我也会遇见何肇发老师,他患有糖尿病。听说他有一次出差,登机后,自己在座位上注射胰岛素。空姐以为他是吸毒的“瘾君子”,把他扭送到机务室,好一会才弄个明白。我每次在大榕树附近遇见何老师时,总忍不住偷偷发笑。这些老师,都是文科的名师,是中大的栋梁,他们风格各异,但都为社会培育了许多英才。 我还常会遇见蒋湘泽教授。他是研究世界史的名家。蒋老师精干矮小,为人风趣。一天,他在“大榕路”上,一边捧着一堆外文书藉,一边嘴上念念有词,而我正在骑着车前往中区。他一抬头,看到了我,就把我叫住。我以为他有事要我帮忙,赶紧滚鞍下车,听候吩咐。谁知他对我说:“我前天在电视上,看见有人说外语。走前一看,原来是你!”我吃了一惊,连忙说:“没有呀!我是在电视台上讲过话,但说的普通话呀!”他说,“不不!也不像广州话”。我知道他在给我开玩笑,嘲笑我讲的是不三不四的“广普”。我也就回敬他说:“我在校庆晚会上,看见过您演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生”。他得意了,连声说:“是呀、是呀!”我又说:“当时演崔莺莺的,是谢文通教授的太太。”他更高兴了,一迭声说“不错、不错!”我说:“不过,谢师母比您高出了半个头,我以为您演的不是张生,而是莺莺的弟弟:欢郎”。他知道我在“反击”,哈哈大笑,一不留神,手中的书掉满一地,我赶忙替他拣起,大家笑着分手。在那年代,康乐园笼罩着一派友爱和谐的气氛,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,让师生们团结乐观,意气风发。 在大榕树附近,我也会碰到戴镏龄教授和师母徐开蜀,他们总是慢慢地行走,也不太说话。戴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担任过中大外语系的系主任,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。在1954年,教育部门把教授的工资级别,分为四级。中大的一级教授有陈寅恪、姜立夫、陈序经三位。二级教授则有容庚、商承祚等二十位,戴老师也名列在内。当时,据说戴老师认为自己是系主任,不应列入,主动退出。(等到“文革”后,学校才又把他补上),我们知道了,都敬佩他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。我们也都知道,他是享誉全国的英语教授,早年留学欧洲,精通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国语言,是著名的研究莎士比亚专家。想不到,后来我竟有幸和他一家成了邻居。 搬进新居不久,有一天黄昏,我在大榕树下,刚好碰见戴老师和师母一起散步。他站在路旁,把我叫住。我赶紧向他俩问好。他对我说:“你写的有关纳兰性德的那本书,我和宗炎先生都看了,也讨论过,写得不错。”我连忙请他多多指正。他却提醒我:“我知道你跟王起先生研究古代戏曲,但诗词这块,你也别掉了!”我赶紧点头领教。那时,让我想不到的是,他是研究外语的专家,但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,也注意到了。后来一想,老一辈的学者,都有很深的国学基础,也自然会关心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。再一想,戴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。早在青年时期,便把莎翁的“十四行诗”,译成中文。和别的译文不同的是,他既注意到英诗的音乐性,又注意到译文要表现出汉语的声韵和节奏。据他的门生王宾教授回忆,当年,戴老师翻译莎翁的“十四行诗”,是译好了一首,便寄给徐女士一首,鸿雁传情,终成眷属。后来,储安平知道了,便拿去一些,发表在《观察》杂志上。我又想,戴老师之所以提醒我,这和他自己的治学经验有关。因为莎翁既是戏剧家,又是诗人。戴老师既研究他的诗,也研究他的剧本,了解对文学不同体裁的研究,应该互相贯通,才能挥洒自如,取得成果。后来,我给自己定下教学和研究的目标:“戏曲为主,兼学别样”,正是得益于戴老师对我的及时指点。 某年冬天,在距离春节的前两天,我又在大榕树下,遇见了戴老师和戴师母。那阶段,我处于困境,心情不好,听说大榕树下,有花农在这里设摊卖花,我也想买些菊花应节解闷。那时,买花的人较多,我只顾选花,却没有发现戴老师,倒是他先看到了我。等到我买了花往回走时,他俩站在路边,把我叫住。我赶紧走了过去。只见戴老师左右张望,欲言又止,摆了摆手,便慢慢地走开。我看着他俩远去的背影,觉得有点奇怪,到底他想对我说些什么?在犹豫中,忽然记起家人吩咐我还要买盆金桔,便回到大榕树下。但是,戴老师当时的表情,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。 过了两天,就是春节。按照中大传统惯例,那天早上,教师们都会自动到小礼堂参加团拜活动,彼此握手,互相祝贺。那年,我没有参加团拜,只在书房里看书。忽然,听到敲门的声音,我想,那年头,有些人见到我,“避之则吉”,不会有什么人来吧?或者有人要找别的老教授贺年,弄错了地方吧?正迟疑间,敲门声又响起,我只好前往开门,一看,愣了,原来站在门口的,正是戴老师和戴师母。师母说:“我们给你拜年来了!”我大吃一惊,很不好意思。按传统,只有晚辈给长辈拜年,哪有长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?我赶紧请他们进屋,倒茶、让座,他们也没有说些什么,只问问我妻子身体情况之类的话,几分钟后,便告辞了。戴师母还在袋子里掏出一盒小点心,说是给我孩子的小礼物。我手足无措,赶紧送他俩上楼,(他家在三楼,我住在二楼)。在他家的门口,我向两位鞠躬致谢。当下楼回到自己的屋里时,眼泪夺眶而出,深深感受到老一辈的教师,对后辈的关怀和理解。过了两天,社会学系何肇发老师,校党委副书记曾桂友,也来我家拜年,他们坐了一会,就到楼下找蒋湘泽老师聊天去了。而老师们的心意,我也领会到了。 在康乐园里,许多老一辈的教授,他们不仅用科研和教学成果,支撑起中山大学的荣耀,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,也着眼于学校整体的学科建设,乃至关心和扶持像我那样,属于不同院系晚辈教师的健康成长。因为,他们把学校作为自己的家园,爱护家园里的一草一木。他们不就是校园里又高又粗的“老榕树”吗?那苍劲的躯干,浓密的树冠,佑护着小树的发育茁壮。杜甫有句云:“霜皮溜雨四十围,黛色参天二千尺”,我想,诗人写那大树伟岸的风姿,遒劲的风骨,也正是康乐园里“老榕树”的写照,是老一辈学者和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的象征。 我爱绿树成荫的康乐园,园里的树,是一代又一代的教职员工,辛勤栽培灌溉的成果。去年,听说广州砍倒了大批榕树,引起市民强烈的不满。砍树之风,不知道有没有吹进康乐园?“毁树容易种树难”,“人挪活,树挪死”,这些历史教训,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。(本文原题《黛色参天二千尺——记康乐园的老榕树》,作者黄天骥,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) |